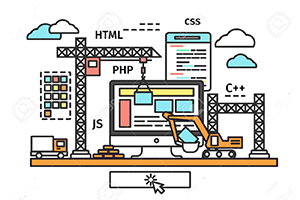校友中心
“我的儿子,他就是没有眼泪”,浙大口腔校友俞光岩有办法!
发表时间:2023-11-17
发表时间:2023-11-17
“我的儿子,他就是没有眼泪啊。”妈妈说。面对重症眼干这项世界性的难题,他以“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症干眼症”,救了许多病人。
重症干眼的病人非常痛苦,浙大口腔校友俞光岩用医疗技术改变了这一现实,他主导开展的,血管化自体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疗效确切,将分泌唾液的下颌下腺移植用它的分泌液替代泪液就能让眼睛重新朗润起来。

俞光岩,教授、博士生导师。1979年本科毕业于浙江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浙大口腔医学院名誉院长。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口腔颌面外科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研究生导师。中华口腔医学会名誉会长,曾任北京大学口腔医学院院长。研究方向为唾液腺疾病,尤其是IgG4相关性唾液腺炎的临床和基础研究;重症干眼症的干预机制及治疗。
总是笑眯眯的俞光岩刚成为一名口腔科医生时,觉得“32颗牙齿,没什么可做的”现在作为一名口腔科大夫治了眼科的病。如今俞光岩已年过古稀,仍在临床一线救治病人,怀揣一颗热忱质朴的赤子之心,一次次施展着他年轻时的职业抱负。
“俞大夫,手术前那晚的谈话,救了我一条命。”
术前谈话,救了他一命
俞光岩还记得,曾有学生开玩笑说:“病人不听话,得治一治。”当时他摆摆手正色道:“要想提高病人的依从性,不能靠‘治’,而是要靠服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几十年前,俞光岩值班时,一位年轻医师告诉他,一位患有早期口底癌的病人不太配合第二天的手术安排。
于是他找到这位病人,将早期癌预后相对乐观、治疗经验丰富的情况与他娓娓道来,言语中既有医生的冷静又不乏朋友般的关怀。病人因此选择了接受手术、积极治疗,最终恢复了健康。
从此,这位病人心怀感恩,常常利用他从事电影公司技术员的职业技能,来为忙碌于病房内外的医护修理冰箱、录音机这些电器,与大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许多年后,病人又一次与俞光岩谈起当年的事。他的眼中炯炯生辉:“俞大夫,手术前那晚的谈话,你的每一句话、每一个表情、每一个动作,我都印象深刻。那一番话,救了我一条命。”
他坦陈,当年看到病历上写的是“癌”,霎时间心灰意冷。他担心癌症无法根除,治疗开销还会拖累新婚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已经做了自我了断的打算。是俞光岩的术前谈话改变了他的命运。
现在,这位病人成为电影公司的技术骨干,由他担任制片人的电影已经上映,他向俞光岩报喜。“病人朋友取得了成就,比我自己获个科技奖还要高兴。”俞光岩话音未落便笑逐颜开。
在几十年的医者生涯中,俞光岩诊治的肿瘤病人还有很多。
很多恶性肿瘤患者在康复后,时隔十五年、二十年,又来到他这里复查。他们满心感激地握着他的手道谢,与他合影留念。俞光岩形容,那时的感受是任何物质都不能替代的。
还有一位口腔多原发癌的患者,因为癌肿反复发生,前前后后做了多次手术。此后他每年春节都会到俞光岩等几位医生家中拜访探望。他去世后,他的女儿和女婿受他嘱托,将这一习惯与新春灯火一起延续着。医生与病人之间的情谊,就这样随血缘传递到了下一代。
在沿途盛放的回忆里,俞光岩感触,“为病人挽救生命、解除痛苦、带来欢乐,是医生幸福感和成就感的来源。”
这种“救人一命”的自豪感,激励了俞光岩的儿子,他也和父亲一样,选择了学医。
重症干眼,口腔医生有办法!
没有止步于口腔颌面颈部肿瘤领域,俞光岩在血管化自体下颌下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领域也为人们所熟知。
干涩、刺痛、异物感,重度干眼症患者眼部往往感到强烈不适。日积月累,他们的视力也会受到影响,甚至可能致盲。
俞光岩曾经接诊过一个年仅九岁的小姑娘。三年前,重症药物过敏反应不幸发生在她身上,引发了史蒂芬-强森综合征,严重损害了她的眼角结膜、口腔黏膜乃至全身皮肤。自此累及泪腺,出现双侧的重度眼干症状。
小姑娘明亮的眼睛逐渐被茫然浸染,她的视力一降再降,最后仅能识别眼前手动。吃饭时她四处摸索都找不到筷子,走路时她也需要母亲寸步不离地搀扶,生活已经不能自理。
但是,医疗技术改变了这一现实。将能够分泌唾液的下颌下腺移植到颞部,导管转移到眼眶,用移植下颌下腺的分泌液替代泪液,就能让眼睛重新朗润起来。
经过单眼手术之后,小姑娘又能独立行走了。半年以后另一只眼也接受了移植。出院以后,小姑娘就骑着自行车上学去了。
俞光岩欣慰地感叹,有效的新技术,真的能够扭转患者的人生、改写家庭的未来。这样的愿望支持着他在治疗重症眼干的征途上笃行不倦,至今团队已完成230多例患眼的手术,在数量上世界领先。
回顾来时的路,俞光岩微笑着,过往的光景还历历在目。1997年,他的学生,也就是现在北京大学口腔医院的副院长蔡志刚教授从德国带回信息,那里的专家把唾液腺移植治疗重度干眼症的目光从腮腺转向了下颌下腺。唾液腺外科正是俞光岩的研究专长。于是他成立课题组,决定将这一项目开展起来。
首先选用家兔进行动物实验,取得了不错的效果。接着对唾液和泪液进行成分分析,发现唾液包含着泪液中的所有成分。腮腺是浆液性腺体,而下颌下腺和泪腺同属混合型腺体,果真是下颌下腺的分泌液更接近泪液。就这样,1999年这一技术被正式应用于临床,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
但这还远远不够。与治疗相关的问题在临床实践中接连显现,俞光岩继而率领团队与他的爱人吴立玲所在的基础医学院病理生理教研室展开深度合作,夫妻二人通力协作,从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层面进一步研究了唾液腺的分泌机制。
由于腺体移植后血管吻合而神经离断,失神经支配的状态下分泌机制有所变化,具体体现在,术后三天会出现暂时性的溢泪期,而此后三个月将进入休眠期,直到第四个月才能趋于稳定。休眠期移植腺体分泌量很少,容易导致导管阻塞。但若腺体大功能好,在移植远期有可能发生泪溢。另外,移植腺体缺乏自然调节机制,所以天气热时或运动过后,泪液分泌都会增加。如何按照需求人工调控移植腺体的分泌功能,成为研究的下一个焦点。
想要小幅调节腺体分泌量,采用药物干预是优选。对于休眠期,俞光岩课题组先后发现了移植腺体表面涂抹辣椒素霜剂和腹部皮下注射卡巴胆碱两种方式,能够促进移植腺体的分泌,有效预防腺体分泌不足造成的导管阻塞。通过药物干预后,导管阻塞的发生率从原先的18%下降为6%。
对于移植腺体分泌过多产生的溢泪,也可通过腺体表面涂抹阿托品霜剂和腺体局部注射A型肉毒毒素两个方法得以缓解,其中A型肉毒毒素的作用可以维持三个月,恰好可以覆盖激发腺体过量分泌的炎炎夏日。
但药物干预在移植下颌下腺持续大量分泌的异常状态下显得有些无能为力。面对移植远期出现的泪溢问题,传统的方法是进行二次手术以切除过多的腺体。要想避免二次甚至多次手术,俞光岩联想到了肝脏外科中的部分肝移植手术——将供体肝脏游离出一部分植入患者体内,或许可供参考。
但唾液腺只有一套血管和导管系统,应该如何在保证腺体功能正常的条件下做到有效分蘖呢?答案就在显微解剖研究之中。从因口腔癌行颈淋巴清扫过程中得到可供实验的正常下颌下腺,把染料树脂灌注进这些盘根作结的管道里,红色是动脉、蓝色是静脉、白色是导管。最后用醋酸浸泡,腺体被脱去,而染料树脂形成血管导管铸型。如此,血管导管系统就清晰地显露出来了。三种颜色的管道并行分布,如同一棵枝繁叶茂的树。这样一来便可以顺着分支,以腺叶为单位分离切除部分腺体组织,保留下来的腺体组织具有较为完整的血管导管系统,这一研究结果为部分下颌下腺移植新术式提供了解剖学基础。
自此对临床判断术后大概率出现重症溢泪的病人,就可以通过减量下颌下腺移植术式进行预防,使针对泪溢的二次减量切除手术率由80%下降到了30%。
一系列临床与基础相结合的研究工作后,俞光岩课题组形成了重度干眼症不同时期、不同情景的治疗常规。
“如果没有全面、精湛的医疗技术,不能解决患者的问题,那厚道行医就成为一句空话了。”
爱岗敬业,矢志不渝秉医心
“当时觉得,口腔里面不就32颗牙齿吗,有什么可做呢?”文革期间俞光岩在上中学,毕业后就回乡做了一段时间赤脚医生。后来他被绍兴地区卫校招收,结业后分配到绍兴地区医院口腔科工作,自此开启了他的职业生涯。最初他对这个分配结果并不算满意,在他的印象里,口腔医生无非就是拔牙补牙,整天跟牙打交道,这种工作堪称索然无味。
但在着手去做和继续求学之后,他最初的看法不知不觉间彻底被推翻。1976年,他成为浙江医科大学口腔医学系的第一届学生,1979年,他又进入北京医学院攻读硕士学位。随着对口腔科学的认识更加深入,他逐渐发现,口腔医学疾病种类多、所涉知识面广泛、操作精细复杂、有时治疗效果立竿见影,其实大有可为。
与此同时,口腔医学的专业范围正在不断扩大、治疗手段不断改进,治疗效果不断提高。让俞光岩印象深刻的是,显微外科的发展使口腔颌面部肿瘤切除后缺损颌骨的功能性重建成为可能。原本术后歪着半张脸、吃东西也只能靠半边咀嚼的下颌牙龈癌病人,现在患者的颜面部外形与咀嚼功能可以复原到和得病前相当的水平。这就是口腔医学专业的魅力,让俞光岩不由得心驰神往。
兴趣使俞光岩数十年如一日地坚守着临床医生的身份,即使如今他已71岁高龄,也仍然不忘在他热爱的手术台上,一次次施展他年轻时的职业抱负。
手术后的男人,在病床上休息。俞光岩走到他的身边。“睡得怎么样啊,晚上病人比较多,不容易睡好。”操着一口温声细语的浙江普通话,俞光岩微笑着伸手,轻轻扶了扶病人的床头。
热情服务的品格、刻苦钻研的精神、敬业乐业的态度,这些都是俞光岩在从业的四十余年中千淘万漉所得到的医道,在日常点滴之中润物无声地,随学脉流长而代代传承。
为俞光岩校友点赞!
内容来源:北京大学口腔医院、北京大学校报第1644期,记者| 王挥闵线